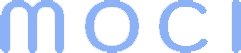树下
在线播放
E1 : S1
故事1:第3集
女人冲着不远处的大树示意道。“我们到那边去吧。我曾在那棵树下坐过。事实上,它认识我。”尽管没有光,男子能听出她正在微笑。
男子点了点头,两位朋友默默走过了这段不长的距离。到达目的地,女人背靠着树干坐下,男子坐到她的对面,水罐被放在2人中间。
“核心一直在深化,”女人开口道。“它永远在移行向‘未知’的方向。同样如此的还有‘主权体’,以及‘主权体’所依赖的‘联合场’。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并非静态的。它在经由时空演化着,而我们就属于这场演化的一部分。我们也在演化,即便是那些深陷于极端危险的最深二元性的人们,他们也在演化,也在为‘联合场’带来一种进化性洞见,展示出某种特定的未来。”
男子叹着气,并未隐藏自己的挫败感。“可历史一次次地重演。如果需要证明,只需去看看战争。难道我们只得承认人类是愚蠢的吗?”
“我们被计划是来将自己的个人化的智慧汲引到表面,并通过我们的‘具象化展现’——我们的创造物——去表现出‘互联’。没有人例外。我们全都作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一枚粒子,完全地献身于了该计划时。完成此事的方式就跟宇宙中的星星一样多。
“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表达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这个世界的的改变是发生在‘全体’层面的,在单个生命期内,这些改变如此渐进,看上去就像压根没有发生。如果我们能校准我们的‘人类性’与‘意识’,表面与核心,头脑与心脏,我们就必然活成‘野生生物’,这即是我们之所是的本质。”
“听起来挺自私……”男子说道。
女人摇了摇头。“当一个人活出‘互联’时,就不存在所谓自私。我们只是活成了‘互联’的一种表达。表达‘互联’的方式,好吧,只能是一种无有限定的行为,不被话语、数字、或任何定义所限制。我的用语并非自己的发明。我并未无视百万计心脏和头脑的用语,以特殊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话语。我使用的每一个词都生自我们每个人。每个人都在说着它。它属于“全体性”,而不属于我。”
“所以,你是在说,你失去了对自身话语、行为,甚至头脑的所有权?”男子评论道。“如果都失去了所有权,你又如何享受生命?”
“再次,我们的本能就是极性化,选择二元性的一极。但我们能够两者兼得。我们能够在体验和表达中感觉到‘主权体’这一侧;同时,我们也能理解,我是说真正地理解,我们被互联着回归我们源头的所有道路,以及通往我们天命的所有道路。我们能够理解,这两种视角能够作为搭档共存。”
“这样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人?”
“甚至“更好”这个词,也意味着‘分裂’。”
“那么你的回答是,并不会,还是…...无关紧要?我被搞糊涂了。”
“我们是主权体,不仅一个生命期如此,而是始终都如此。主权体是生命期的混合物,积分态则是主权体的混合物。美丽钻石的一个琢面并非整个钻石,但它却携带着一扇窗户,通往钻石核心。我们必须就始于这核心。一旦以这样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位置,你就会看到,所有权是无法被确定的。那就像在试图钉住永远流动的风。创意、创造性、表达,最初都升自哪里?在它们生自的那个时空,它们又是被如何解释的?那个时空是先于还是后于我们时空,又或者是同时出现的?
“拥有了这个地基,我们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,去看向个别化生命期及其实相。在那个实相中,我们是人类,有着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。在那个实相中,我们能够体验和表达出我们的‘互联’——那种‘被统合’的感觉,每一个生命,无论对于整体还是对于个体,都是宝贵的,这是完全独立于人类判断之外的。换句话说,我们能够两个视角兼有,这就是我要表达的重点。”
男子身体后仰,以双臂撑住自己。“你之前提到主权体时,我以为你是指……我。我是主权体,但刚刚,我看到了一个新定义的出现。我所隶属的主权体是时空二元性中所有“我”的混合物。在某种意义上,我一直存在着,从时空的第一纳秒直到现在。当时空折叠进非-时空,我们的天命就是身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而遍存于全体中,‘我’也会存在于‘全体’中。我正确理解了你的意思吗?”
“是的,我想要补充的是,‘全体之天命’即是‘个体之天命’,同样的,‘个体’的创造物即是‘全体’的创造物。这种流动和运动是分形化的。它运作在时空二元性的全部层级。对于没有基于‘互联’这个目的而彼此搭档的头脑和心脏而言,这样的视野是无法想象的。然而,一旦这个视野被清晰想象出来,它就会像精确制导系统,逐渐地流入你的生命。你会开始看到,它在照料和负责你实相中的全部事物。”
男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手,喃喃自语着模糊不清的话语。“我们又回到了心脏和头脑的搭档关系。为什么?为什么这种总是被提及?”
女人以手碰了碰一侧的太阳穴。“科学家告诉我们,我们的大脑拥有约860亿个神经元,我们的肠道拥有约5亿个,我们的胃有1亿个,而我们的心脏有4万个。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是心脏的210万倍。我们的大脑在‘人类性’中处于主导地位。可是,我们的感觉中心则是由心脏、肠道和胃部区域构成的,这个感觉中心,会在神经和能量层面通信于我们的大脑。
“我们意识与心智间的通信,心智与大脑间的通信,大脑与心脏间的通信,心脏与意识间的通信;这些就像一种交响乐的乐章,能够流动地和谐、非和谐,或是两者兼具,而且,这流动指向所有的方向。当这些交响乐乐章处于和谐时,我们就广播出了‘互联性’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“既然都理解了这一点,”男子说,“我们为什么还会倒退去传播‘分裂’及非和谐?”
“因为‘全体性’,亦即我们全体皆是的‘积分态’,它在时空二元性中的运动是基于平衡的步调,就像手风琴风箱一样徐徐地拉开。在这过程中,我们拥有自由意志。我们做出决定。或许我们跟‘全体性’之间的连接会说服我们扮演一个‘分裂’的角色,以防我们过快迈向我们的天命。我们希望避免瀑布般一落到底。源自我们最高的心脏和头脑,我们潜意识地感知到了这些,而我们则会听从它。
“这也是对于‘互联’的理解的一部分。‘互联’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构建或新时代概念,只因着其表面吸引力而被四下谈论着。它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,因为它是......它的深度和广度是扩张性的。你能够花上一生来探入它的深度,却永远找不到它的底部...或天花板,甚或一堵墙。
"但这需要花费时间,"男子说道。"似乎没人有足够的时间或兴趣来思考这个问题。"
"这正是为什么,一些人会化身到这里,来将这些概念编码成文字、图像或声音;来创造出一种可能,以便我们任何人,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能置身‘分裂’之内去体验到‘互联’。不是试图支持‘互联’而远离‘分裂’,而是积分整合起‘分裂’;将其视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中的“全体性”的一部分。”
男子又为女人倒了一掬水,因为听得出她的声音有些发紧了。
喝完水,女人仰向天空,望着漫天繁星和新月。“我们曾仰望夜空来提醒自己,我们的浩瀚,以及我们生活之处的浩瀚,现在却慢慢变成了凝视科技屏幕来提醒自己,我们世界有多么微小。这种差异是显著的。而科技只会变得更加弥漫且具侵入性。
“为了与科技共存,我们需要尊重它。科技能够将我们引导向‘互联’,就像它能创造出各种‘分裂’世界,将我们收集进各个数据分组,滋养我们的兴趣去喂食经济。在时空二元性中,它两者皆做,之所以两者皆做,是因为我们集体的决定。”
男子喝了一口水,目光游弋于女人身周。
"你的水罐呢?"他突然问道
"我没带水罐。"
"那你怎么取水?”
"我内里携带着它带,"女人微笑道。
男子递过自己的水罐。“给。我回村里再弄一个。”
"不,谢谢。我自有办法。"
男子放下水罐,看进女人的眼睛里。“如果我是主权体,是核心,是那个生活于所有经历和表达中的生物,如果我是这个,但又是单个生命期内的人类个体,我怎么才能......怎么才能理解这个?"
女人展开双臂,仿佛在拉直一根线。"这就是主权体,"她解释道,然后以右手沿着想象中拉直的线一路碎切下去。"而这些则是每一个生命期。"
然后,女人探手伸入这条想象的线,以食指和拇指捻起一个想象中的小人,将其提到线的上方。"你,是一个生命期,主权体不是一个生命期,它是所有生命期的混合物,它是贯穿各个生命期的‘联合之线’。这就是属于主权体层面的‘全体性’。而因为每个主权体均是如此,所以,还存在另一种‘全体性’,使得我们被互联地生活在一起,无论我们知不知道它。"
女人凑近了些,低声道。"但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种‘全体性’,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看到‘互联’,在每一个当下,以足够的细节。我们看到了它。我们惊叹于它。我们对之大笑。我们全心地爱它。无他,我们仅仅只是识别出了‘全体性’的存在。有些人称之为同时发生、同步性或奇迹、大宇宙微笑或宇宙的微笑、事件之弦或命运。无论怎么称呼,你遭遇了这些词,并且,你正在考虑它们对于你单个生命期的价值。"
“我还要说的是,这些词不仅仅适用于单个生命期,也适用于主权体。我们创造的每一个事物,我们遭遇的每一个‘具象化展现’,都是主权体在流经我们,荣耀我们的‘整体性’。我们化身进了单个生命期,但我们也具象化地展现出了‘无限性’,这正是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的。‘无限’跟‘有限’是一种搭档关系,就好像‘无限’正在租用一个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来生活于这个时空中,不是来体验和表达出‘互联’,就是来体验和表达出‘分裂’,又或者,同时体验和表达出两者的搭档关系,这一点很重要。”
"搭档关系?"男子问道。“你怎么才能将这些对立元素,如此根本对立的元素,带入搭档关系?”
女人能感受到对方语调中的质疑,她记起自己一度也生出过同样的语气,于是选择了微笑来表达出自己的接纳。“跟对待任何二元性一样的方式,我们不评判。如果不评判,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搭档关系,如果形成了搭档关系,我们就不会评判。我们不评判,相反,我们会找出‘互联’的信号;我们会找出我们主权体通信于我们——人类自我——的种种方式。”
“所以,你在说,”男子道,“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可见的意识,它活在于许多许多的生命期中,它才是‘我真正之所是’,而其他每一个生命也都拥有类似的不可见意识,在这一点上,我们全体被互联在了一起?这个意识,你称之为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”?是这样吗?”
“是的,这正是我要表达的。我们被赋予了选择权,去实验如何将关于‘互联’的理解带入这个世界,或是去实验如何源于一种‘分裂’视角而生活。要么选择,我们是单个有限生命期内的一个意识,拥有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;要么选择,我们是自身无限性的一枚化身粒子,是自己创造出的‘整体’的一个部分。”
“无论如何,如果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体——编织进所有生命期的‘联合之线’,同时又保持一种‘一体性’的感知,我们就能存在为一个‘主权性积分态’,在时空二元性中的具象化地展现出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不会完美,但却知觉到,并校准于我们的根基性的‘联合’。
"为什么会不完美?"他问道。
"因为二元性制造出评判,评判又制造出二元性。它们是自我-强化的,结果就是迅速的演变。在地球上,我们处于时空二元性的‘浓汤’里,所以我们会评判自己,评判我们的‘具象化展现’,我们创造的事物。我们在表达上是不完美的。但是,在‘互联’中并不存在评判。要在我们的核心与表面之间、主权体与人类自我之间形成搭档关系,这就是唯一的途径。我们必须摒弃‘评判’,但又保留下经由‘搭档关系’这个镜头,无评判地阅读我们实相的能力。"
"那么,这种搭档关系需要些什么?"
"一种意愿,不,更像是一种勇气,勇敢地在单个生命期内活成独立的人类存在体,并体验这个过程。勇敢地体认到你同时是搭档双方;你不会受制于其他人或其他时空的言语评论。即便这份体认以及对它的‘具象化展现’,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极端价值观,那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在绝弃掉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,就像士兵扔掉了自己的盾牌。
"这就是那些人要扮演的角色。一个角色无所谓好坏,它只是必不可少的,否则它就不会存在。它是平衡的一部分,是在推动我们物种平衡地移动向‘互联’,哪怕看上去它正在陷入更大的‘分裂’中。
"他们的评判话语会出现在我们的头脑和心脏里,这个事本身表明,我们正在移动向‘互联’的方向。他们的话语仅仅体现出了他们对于‘我们在内在被互联着’这件事的理解。而且,是的,在你提问之前,我会先说,观点会转译成行动,转译成行为。行为只是感知的一种反映。我们如何感知自己的实相影响着我们的行为,而这又直接影响着我们自己的实相。
“因此,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实相内感知到‘互联’,我们的行为和‘具象化展现’将反映出这一点。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一直在散发,不是为了改变任何事物,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价值观,不是为了转变任何人的方向。它仅仅只是在演示出我们全体共享的‘全体性’、‘积分性’和‘互联性’。在这么做时,它完全理解,‘分裂’将会加深,从而提供一种平衡,这全是‘联合’与‘全体性’的一部分。”
男子手抚住水罐,手指在上面轮弹着。这是‘烦躁’的身体语言。什么事正困扰着他。“那么,我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生活。我不得不同时是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。并且,我不得不在所有这一切中以某种方式保持神志清明。怎么做到?我理解了为什么,对我而言这讲得通,可我该怎么做?这个部分,无论我多努力去理解,都完全不……”
男子停下手指,寂静重回了树下空间。远处井边传来其他旅者取水时的话语声,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宽慰感。
“当你学习某事时,什么是最根本的前提?”女人问道。
“花费时间并且练习。”
“只要给予一个新事物以时间和练习,你就能学会如何做了吗?”
“……是的,通常吧。”
“你学习的程度,受限于你的天赋,那什么又是天赋呢?”她问。
“那是一种礼物……嗯,我不知道。我一直被告知,某人在某方面拥有天赋,是上帝的礼物。”
“天赋,正如我们被教导的那样,是悟性与信念的融合,然后,在时间和练习的镜头下,它的结果开始展开。结果则呼唤着更多的时间和练习,甚至可能会将你拉入‘未知’,那个无人冒险进入的地方,只有你能去往的地方。这就是天赋!你冒险进入了‘未知’,扩展着特定学科的实相,比如角色扮演、绘画、艺术表演、写作、爱、歌唱,或者仅仅就是生活本身。你经由天赋扩展了这些。整个宇宙中都没有人确切地理解,你的天赋会将你引向何处,它会如何浮现。在你的实相和时空里去理解和扩展某个学科,这是属于你个人的事。”
她停顿了一会儿,端详着自己的手,它们几乎消失在了渐增的黑暗中。“至于你如何做到......在体验和表达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时,在移动于2者之间,如何保持神志清明,这即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天赋。你的天赋即是艺术性地做到这一点。这件事,我们全体都在做,每一只昆虫,每一株植物,每一个动物,每一个人,存在于时空二元性里的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生命。
“余下的一切,你在这个世界里拥有的每一项技能、目标实现、长期成就、独特优势,这些都是你与某个学科的共鸣,这共鸣可能源自你的身体、头脑、心脏、或某个平行生命。谁知道呢?这些共鸣会激发出你的激情。在哪里拥有了激情,你就会将时间和练习分配到哪里。
“不过,别将共鸣混淆于天赋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。我们的天赋就是:知道在自己实相内如何去平衡这对根本的二元性——‘互联’和‘分裂’。不是去平衡别人实相里的二元性,而是我们自己实相里的。”
男子的手指再次敲动起来。“这种天赋来自哪里?”
“你已经拥有了它。你已经在运用它。天赋是个人化的。它无法被评判。每个生命和每个事物都有这个天赋,容许他们去发现‘分裂’与‘互联’的平衡。这种平衡被发现于何处,又如何表达出来,正是这些造就了我们的独一无二性,以及我们对于‘整体’的富于价值的贡献。”
“所以...所以,你的意思是,”男子说道,“我们所有人都拥有同一项天赋,这天赋就是,当我们在自身实相的时空中做选择时,如何流动于‘分裂’和‘互联’这两种存在状态之间。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平衡,这就是我们的天赋。我正确理解了吗?”
“在某个层面,是的。”
“那么,你的意思就是,我们的天赋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就这么简单。这就是我们的天赋?一个在大街上行乞的无家可归的战场老兵,也拥有生活的天赋?”
“你谈论的是‘分裂’的胜-负幸存游戏,”女人说道。“而非天赋。所有的‘具象化展现’,无论他们是否具有觉知力,都拥有一个共同之处:他们拥有天赋去为自己的物种发现根本二元性——‘分裂’与‘互联’——的一种平衡,一旦这种平衡被达成,它也更容易在全部物种内的所有地方被达成。这种平衡是独一无二的,过去从未以同样的方式达成过。
“千真万确地,每一个当下,这种平衡都在变动着。对于‘个体’、‘众体’、和‘全体’而言,其平衡永远都是彼此不同的。这正是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的部分含义。在所有层级、所有地方、所有时间,我们都共同地处于这种动态平衡中。如果能想象出这种动态平衡,你就能部分理解它,因而,就能为自己找到一种更舒适的平衡。
“你看,”女人继续说道,“这就是我们能在每个存在体身上识别出来的天赋。因着这种识别,我们能够创造出感激、慈悲和理解,仅仅是因为,我们观察到了,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保持个体的及集体的平衡。那些‘分裂’占比更高、‘互联’占比更低的人们并未阻碍那通往和平、和谐世界的进程,他们通过自身的天赋来平衡着我们的进程。
“当然,这种视角要被获得,只有当我们充分地意识到了:我们如何地全都是‘全体性’的一部分;只有当我们回忆起了: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条‘联合之线’,而不仅仅是竞争于单一幸存游戏中的肉与骨。”
女子合上了双眼,变得完全地静止。看上去她深埋进了周围这寂静、止息、深邃黑暗的怀抱中。只有亿兆星星和半只月亮的微光映照在她的脸上。
男子也闭上双眼,深深吸入了一口气。
“只存在着一种天赋,这个天赋就是:‘个体’,以一种放眼整个无限时空都独一无二的方式,去逐渐变为了‘全体’,同时又维系住自己的平衡。走钢丝的人能变得如此精于自己的技艺,几乎能在钢丝上小跑。可是,如果行动得太快,无论多么娴熟,他们都会摔下来。我们也是如此。在旅行过时空二元性时,其余所有的二元性,像是快乐与悲伤,成功和失败,都仅仅只是在娱乐和引导我们。”
男子略微讥讽地笑道。“看起来,你能拿这样的概念为可怕行为辩解。你总是可以说:‘发生的一切,都是为了给我们所挚爱的物种提供平衡,尽管来吧。’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讽刺。
女人会意地点了点头。“有些时候,在某个群体或个体内,‘分裂’占比变得如此之高,以至于他们失掉了平衡,进而做出不堪想象的事。这些就不是天赋了,而是失衡,是天赋的反面。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慈悲。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,能够实实在在地理解:‘分裂’的极端占比可能会如何地诱发毫无必要的破坏行为。”
“尽管如此,在‘一体性’的最为广大的俯瞰视野下,那仍然是‘整体’的一部分。整体的平衡依然是毋庸置疑的。只有该个体或群体的平衡变得存疑,当一个人愈发分裂于其他的生命表达,他们的平衡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。
“在对‘互联’的感觉和专注中,就能够发现‘舒适’。‘舒适’是一种流动的感觉,一种连接上‘更大智能’及‘持续扩展中的理解’的感觉。我提到的这种‘舒适’与‘意识’相关,而非生物学的‘舒适’。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。举例而言,我是个老人,我的身体在它有意识的几乎每一刻都在隐隐作痛,一个刻又一刻,仅仅是程度不同。然而,我的意识却能够一直流动,如同微风拂过草原,在那里动物、植物们都生机勃勃。我能够一生都如此。我需要做的全部就是理解这件事,这种理解将忠诚地找到一条路,通往我们的思想、感觉,并最终进入我们的行为——我们的实相。”
“啊,行动才最重要,不是吗?”男子评论着,语调却是疏离的,仿佛陷入了沉思。“可是,正是在这件事上,我们比其他任何事都更为挣扎。为什么呢?”
“因为我们没有理解,而且通常这又是因为,我们不愿意去理解。”
“为什么会这样?”男子问。“对我而言,这没有道理。”
“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平衡需要维系。还记得吗,我们的天赋?”
男子点了点头。“记得……”
“如果每个人,每个人类存在,突然间都转变到99%的‘互联’占比,‘分裂’只占1%,你觉得会发生什么?”
“我们的世界会改变……?”
“我们的世界会陷入混乱,”女人即刻纠正道。
她自顾自笑了起来。“我给你讲个故事。我曾认识一个人,他还有点像你,他曾要求我证明,‘行动’比‘思想’更强大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。这不是显然的吗?所以,我让他想象自己在打我,然后我也同样地回应他,不过则是以行动。然后我们就能裁定哪个更为强大。”她因这回忆笑了起来。
“令我十分惊讶的是,他接受了我的提议。于是,当挑战开始时,他闭上眼睛,要求我10秒钟后再打他。这是个合理的请求,所以我就等待着。过了约10秒钟,他举起了手,好像在说……来吧,打我。可我没有兴趣打他。我不可能打他。我不愿打他。对我来说,打他是不可能的事。
“事后,我问他,那10秒钟里他在想些什么,他对我笑了笑,问了我同样的问题。这时我明白了,那时,他思想和感觉所形成的心理球状空间包围了我,而我则会听从,因为在那时,他是我敬重的老师。我别无选择。而他也知道,我是以这种方式看待生命的,而且,我会听从他的思想和感觉,即便那是无声无形的。
女人停顿了下,食指指向男子,直视着他,说道。“永远不要相信,相比于行动,我们的思想和感觉更为无力,又或者,你可以这样去思考和感觉,却采取那样的行动。它们是同一生物的两条腿,它们总是一起动作。它们是同一事物,即便显得并非如此。对于主权体而言,它们就是同一事物。只是因为思想和感觉通常先行出现,随后才是行动,所以,思想和感觉算是催化剂。它们是强有力的搭档。如果它们被聚焦于‘互联’,它们所催化的行动也将是‘互联性’的。”
女人稍稍借助着树干的帮助,费力站了起来。男子也随之站起了身。松树的第一层枝干距离地面约7英尺,如同天国探下的巨手悬在他们上方。“我只能坐这么久,已经好晚了,我的朋友。希望我们再次相遇时,不是因为饮水出了状况。”她微笑着转过身,移步离开。
“等等!”男子几乎喊了出来。“难道你不带些水?你可以拿走我的。我会到镇上买个新罐子。”
女人回过身,摇了摇头。“我自有办法。水会找到我的。”
男子跑向她。“拿去,来吧,我依然坚持把水罐留给你。对我来说,再弄一个比你容易。”
“或许是这样的,不过,当需要水时,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更多。”她轻抚了一下男子的脸颊。“不过,谢谢你的善意。”
女人重又转身离去。男子看着她消失进夜晚的空气中,如同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滑行于各个黑暗世界之间。
直至对方消失进黑暗,男子才举步离开,只感觉手里的水罐变得沉重。
一个陌生人伸出胳膊向他走来。“如果太重了,我倒可以帮你减轻些负荷。”对方友善地咧嘴笑道。
男子将罐子递了过去,陌生人喝了几秒钟,恭敬地递还水罐。
“谢谢你,”陌生人拿袖子擦了擦嘴。“刚才跟你聊天的女人是哪位?”
男子因为这个问题后退了一步,完全没意识一直有人在看着他们,“你是谁?”
“我是个陌生人。”
“你叫什么名字,陌生人?”
“这个名字就不错。”
“你想让我叫你‘陌生人’......嗯......你偷窥和偷听我们的对话多久了?”
“我就在大树背后。”陌生人指着他们刚才谈话的大树说道。“我能听到每一句话,但什么都看不见,不过我能告诉你的是,每次你们喝水时,我都变得更加干渴。”他如同一个感叹号点起了头。
“这可是私人谈话,你就不该说些什么吗?”
“比如?”
“嗯......比如告诉我们,你在那里。揭示你的身份。”
“我刚刚不是做了吗。我只是不想打断。我发现这是非常......非同寻常的对话。她是哪位?”
“我只见过她一次。从来没问过她的名字。”
“可是一遇到我,你立马就问了。为什么呢?”陌生人问道。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“她这样的人,你可不该失去联系。她是一位先知。”
“先知?”男子惊讶地重复道。“她怎么就成了先知?”
“看上去她似乎知道未来。”陌生人说。
“我不认为有谁能知道未来?”
“也许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,但最终会发生什么......她是知道的。”
“嗯......”
“无论如何,”陌生人说道,“谢谢你的水。我得继续赶路了,前面还有很长的路等着我。”
“请原谅我的问题,”男子说道,“但我很好奇,对你来说,我们的对话有意义?”
“你问的每个问题都深得我心,她的回答也很有道理,但我无法说清,怎么个有道理法,或者为什么有道理。那就好像......就好像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,如此之简单,要理解它反而变得复杂,不太是因为事情本身复杂,而是因为我内在携带着这种复杂性。事情如此简单,反而提醒我看到了这一点。”
“对!完全正确,这正是我一直试图理解的。如何放下我所学到的复杂性?”
“不学习反倒是件难事,”陌生人摇着头说道。“我们必须自愿放手旧事物,为新事物腾出空间,我们谈论的可不是系鞋带这样的事,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理解,关于‘我们是谁’,‘我们全体是谁’。”
“你做到了?”男子问。
“并未。”
“为什么?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它的价值?”
陌生人想要说话,但停了下来,然后吐出了一口长长的叹息。“我觉得,她谈到的‘平衡’是对的。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放下旧有复杂性,它们萦绕在我的头脑和心脏里。我依然不得不玩幸存游戏。我的生活依然遵循着某种社会习俗的变奏。我无法在一个魔幻瞬间放下这一切。”陌生人弹起响指,发出一串响亮的连音。
男子将水罐放回地面,表示出自己决定停留一会儿。“但她的话触动了你?”
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,抱起双臂,仿佛正在将这问题纳入沉思里。“让我们这么说好了,我对它保持敞开,而我并未敞开的那个部分,将不得不等待。再者,按她的说法,我早已知晓了。它只是一段需要我回忆起的记忆。即便在我准备的过程中,它也仍然在那里。”
说完,陌生人指着水罐道:“走之前我能再喝一口吗?”
男子点了点头。“好的。”
陌生人喝了一大口,将水罐放回地面。“就像承诺的那样,我减轻了你的负荷。感谢你容许我这样做。”
“很高兴能够分享。”男子说。
“我为偷听你们对话而道歉。如果能让你稍感安慰的话,事实上,我先于你们到了树下。我睡着了,而你们的声音吵醒了我,当我醒来,就只得这么听着。只是听着。实际上,你的声音也是我的。你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想问的。所以,感谢你。”
男子点了点头,评论道。“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敞开的头脑。”
“并不完全是,”陌生人打趣道。“并不比别人更敞开。”
“我觉得你不是普通人。”男子说。
陌生人靠近男子,将声音压至微弱的耳语。
“有如此多人对此保持着敞开,如此之多。”
他转过身,离开了。留下他低声的话语悬浮在空气中,如同黑暗天空中醒目的云朵。